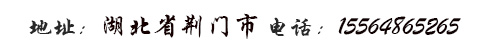落花生
|
北京中科中医院好不好 http://pf.39.net/bdfyy/tslf/150928/4703211.html 落花生,其实就是花生,也叫长生果、泥果子、番果。据说,中国花生产量最大,品质以山东为最佳。 我所住的小县城,最近开了几家“山东炒货”店,花生自然是必备的。店里的花生种类颇多,有水煮花生、鱼皮花生、五香花生、素炒花生等。那种小粒素炒的花生,醇香、嘣脆,口感不错,我特别喜欢。 妻对花生颇为不屑,她喜食坚果、罗汉果等,见我买花生,总是挖苦我:“花生有什么好吃的,你就知道图便宜!”我知道她的哲学:宁买贵的,不买对的。大约女人都是如此吧,我笑了笑,也不争辩,心想:自己喜欢就好。 我对于花生的喜好,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。那时,农村还处于大集体时期。记得每当到了八月初,生产队就好扯花生了。先天晚上,在鱼石刘氏祠(那时改成了仓库)召开社员大会。会上,生产队长反复强调,明天扯花生的纪律,其中,最重要的就是管好自家的孩子。 孩子哪里能管得住呢?何况,在那个年代,父母也不愿意去管。大家心知肚明,趁这个时候,让孩子打打牙祭,挺不错的。 第二天清晨,随着一声声尖锐的哨音,社员们,有的扛着齿耙,有的挑着箩筐,有的背着竹篓,有的拿着凳子,在晨光熹微中,往村子前面的沙洲聚集。 沙洲在泸水河边,平整而开阔,花生苗与杂草共生,满眼的绿,宛若海洋。 见人到齐了,队长便招呼大家,分组一字排开,男子在前,女子在后。男分工明确,男的负责挖花生,女的负责扯花生。 队长清了清嗓子,啰啰嗦嗦,说了一大通:什么要挖干净呀,扯干净呀,某某负责挑花生,路上不要让小孩吃。末了,一声令下:“开挖”。只见,银耙挥舞,笑声、唠嗑声,此起彼伏,好不热闹。 孩子们来了,起初是一个或几个,然后是一群,都远远的,站在樟树下眺望,有几个的嘴里竟然还发出了“咕噜”的声音,估计是在咽口水了。 挑花的过来了,满满一担,扁担一起一伏,发出“嘎吱,嘎吱”的声响,也吸引着我们这群孩子的目光,一颤一颤的。但孩子们终究不敢过去,只能望“花生”兴叹了。 忽然,我灵机一动,前面石桥边,那些花生是一定要在那儿洗的。于是,我们陆陆续续来到石桥边,果然,他们在那儿洗花生,我们凑过去帮忙,七手八脚的,时不时往嘴里塞一粒花生,就着壳吃,甜甜的、香香的,甭提多美味。 能从容地吃一回花生,要等队里扯完了花生。我们扛着锄头,提着竹篮子,在花生地里掏。每当掏到花生,那个高兴劲呀,就别提啦。也许是大人们有意留一些吧,不大会功夫,我们都会满载而归。接着就是清洗、入锅,放上水和盐,再烧火煮。我和弟妹们,围坐在灶边,眼巴巴的,等着花生煮熟。 花生熟了,揭开锅,清香满屋,我们也顾不得烫,抓一把花生,嘴里哈着气。看着我们的馋样,母亲笑了。 队里的花生晒干了,会按人口,分一些给社员。我家那时有五口人,照例也分到了几十斤。花生是父亲挑回来的,母亲先倒一些出来,剥花生米,炒了给父亲下酒,当然,我们也可以吃点,剩下的都装进了坛子里,准备待客或过年用。 现在想想,那时的花生,对于我们而言,那是多么难得的啊。 后来,我读高中,读师范,甚至参加了工作,好吃的有很多,但对花生的喜爱,却一直都在。也许,我喜爱的不是花生本身,而是那段岁月,那抹乡愁吧! (作者:刘新生,笔名:鱼石散人,江西省作协会员。)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luohanguoa.com/lhgyf/74175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罗汉果甘草清莹茶女孩可以喝吗漯河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